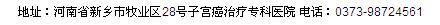大家钱理群谈鲁迅与医学
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北京大学退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
作为我国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鲁迅一生以笔伐戈。但无论是他的文学作品还是他本身,都似乎与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统计,鲁迅一生写了33篇小说,其中20篇都写到了疾病与死亡。10月29日,著名人文学者、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开展了一场关于鲁迅和医学的精彩讲座,引领大家一起探究医学和其背后的“人学”哲思。
1学医、弃医
都抱着“诚与爱”之心
虽然同样是关心人,关心国民的健康,但此时鲁迅的重点却从生理上的健康,转向心理的、精神的健康;将医学问题转化成了一个文学问题、人文问题
很多人都很清楚鲁迅的“弃医从文”,但其实他人生中还有一次职业转换,是“弃矿学医”。鲁迅中学时读的是南京矿路学堂,后来他去日本留学,一开始还保留着对矿务的兴趣,曾经和同学合编过一本《中国矿产志》。但年,24岁的鲁迅转行进入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读了不到两年,年又自动退学,“弃医从文”。鲁迅这样的职业转换,大概很难为今天的国人所理解。我们不禁会问:鲁迅当年为什么要“弃矿学医”?后来为什么又“弃医从文”呢?
先说“弃矿学医”的原因。鲁迅曾经这样谈到自己的“医学梦”:“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期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维新的信仰”。这里,包含了两层意思。首先是鲁迅个人的童年创伤。鲁迅写过两篇文章谈父亲,其中一篇是《父亲的病》。他写直到父亲临终前,自己才突然感悟到父子之间的那种刻骨铭心的血缘关系,却只能大声疾呼:“父亲!父亲!!”多年后,鲁迅还能听到那时自己的喊声,“每听到时,就觉得这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因为打搅了父亲最终的安宁。正是这样的童年记忆,成为鲁迅要“弃矿学医”,而且是西医的最重要的动因。在《父亲的病》里,他在详尽回忆庸医的荒诞与误人之后,还深情回忆一位西医对他说,医生的职责是“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他由此看到了西医的科学性和人情味。
当然,鲁迅的学医也有时代的原因,这就是他所说的“战争时便去当军医”的梦想。研究学者告诉我们,在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人普遍有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并且有一个自我命名,叫“东亚病夫”,认定中国随时有“死亡”的危险。而“东亚病夫”,首先是身体的病弱。这样,强身健体就成了救国的第一要务。在那个时期,从康(有为)、梁(启超)开始,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和知识分子都提倡各种身体改造,提倡“军国民运动”,所以医生就自然成为最被看好、备受尊敬的职业。而这样的尊医、学医的风尚也自此一直延续了差不多一个世纪。
那么,鲁迅后来为什么又要“弃医从文”呢?其实,鲁迅到了仙台不久,就对医学生的生活感到不能适应了。他在写给老同学的信里如此抱怨:“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德语)种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又说:“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锢。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他特别不满意的是自己没有时间阅读与翻译文学作品,他的文学的无羁的想象力,活跃的思想力,显然不适应一板一眼、严格、精密的医学学习方式。而在这其中,让他最不安的还是解剖尸体:“尤其对于女子和婴孩幼孩的尸体,常起一种不忍破坏的情绪”。鲁迅太容易动感情,显然不具备医学必须的冷静。更有意思的是,近几年在日本找到了鲁迅当年画的解剖图,人们惊讶地发现,为了让人体看起来“更美”,好多人体部位都被鲁迅有意改了。这样美学家的眼光与趣味,距离科学家就太远了。还是鲁迅称为“恩师”的解剖学老师藤野严九郞先生最了解他:“大概学习医学本来就不是他出自内心的目的。”学医更多的是出于对家人、国人的责任,所以鲁迅的“弃医从文”,是有内在的原因和逻辑的。
当然,外在的刺激也不可忽视。大家熟知的“幻灯事件”发生在鲁迅的微生物学课堂上,当时老师正在演示日俄战争的时事影片,鲁迅突然在画面上看到“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鲁迅受到极大刺激,他的医学梦因此轰毁:“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虽然同样是关心人,关心国民的健康,但此时鲁迅的重点却从生理上的健康,转向心理的、精神的健康;将医学问题转化成了一个文学问题,人文问题。他与最为相知的许寿裳之间有很多关于人性和国民性的讨论,其中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有研究者因此提出,“诚与爱”是鲁迅思想与精神的核心,他当年怀着“诚与爱”之心去学医;现在又以“诚与爱”之心去改造、疗救国民性。看上去“弃医从文”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但在“医”与“文”之间,还是有内在的统一的。
由此,鲁迅慢慢形成了他“改造、疗救国民性”的文学观:文学“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他的取材,“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里的医学用语:“病态”、“病苦”、“疗救”等等,都成了一种隐喻,它不仅显示了在鲁迅的视阈里,医学与文学的相通,更暗示着医学本身的社会学、政治学的意义。而且如研究者注意到的那样,这样的“疗救”文学观,在中国现代文学里,是占据了特殊重要地位的。许多医院为题材,充满了疾病与死亡的隐喻,如丁玲的《在医院中》,巴金的《第四病室》等等,这都不是偶然的。
“鲁迅当年怀着‘诚与爱’之心去学医;现在,又以“诚与爱”之心去改造、疗救国民性。”图为鲁迅(上排左一)在日本学医期间与同学的合影。
2“疾病”、“死亡”
揭露人性和社会的命题
鲁迅小说里写到的病,大都呈现出一种不确诊的模糊性,“药”则经常处于缺席状态。这种情节结构的处理,是他对文学家所承担的“思想-文化”医疗工作者的角色有着深刻的怀疑
在鲁迅的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同时也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开端的《狂人日记》。小说一开头就有对主人公心理的一段描写:“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这显然是一个受迫害臆想狂的精神病患者,但字里行间又似乎隐含有某种寓意。全篇小说就在这两者的张力中展开。以后,鲁迅又写了《长明灯》和《白光》,也都是写精神病患者的故事。如果再作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狂人日记》和《长明灯》里的主人翁,其实是那个时代的先觉者、先驱者,人们不理解,就把他们看作“疯子”。这类小说的主题是:谁才是真正的病人。而《白光》的主人翁却是因为参加科举考试屡屡失败,真正发疯落水而死的。它的主题指向:谁是身体与精神病害的制造者。
而大家在中学都读过的《药》,就把这两个主题合二为一了。小说有两个故事:一个是茶馆老板的儿子华小栓,患了肺病,他父亲在刑场上求得“人血馒头”来给他治病,结果反而把病耽搁了:这是一个身体与精神双重疾病而死亡的悲剧。小说真正的主人翁夏瑜也是一个先驱者,他想用“革命”来治中国的病,却被他想拯救的得了愚昧病的中国人看做是“疯子”,连他牺牲流出的血也被当做药吃掉了。小说的标题《药》具有两重意义:一是实指“人血馒头”,这是愚昧的象征;另一是虚指革命者给中国开出的药方,暗示老百姓不觉醒,革命也救不了中国。这是一个疗救无望的更大悲剧。
鲁迅还有一篇很特别的小说《兄弟》,写兄弟俩平时感情非常好,弟弟突然发高烧,当时正在流行猩红热,哥哥因此焦虑万分,专门请了一位著名的外国医生,最后诊断是出疹子,不过虚惊一场。这个普通的疾病故事,是以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类似的经历为本的,但鲁迅却虚构了哥哥的一个梦:弟弟真的死了,留下的孩子成了自己的负担,又自认有了任意管束孩子的权利,因此出手把弟弟的孩子痛打了一顿。鲁迅显然运用弗洛伊德的学说,通过梦揭示了人的潜意识:尽管“兄弟怡怡”,但在利益面前,还是掩饰不住人的自私本性。这或许是更为严重的内在疾病吧。可以说,鲁迅是在“疾病”与“死亡”这一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生存境遇里,发现了一个最能展现人性和社会问题的广阔天地。鲁迅一生写了33篇小说,其中20篇都写到了疾病与死亡,占了60%以上。
研究者在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以后,发现鲁迅小说里写到的病,大都呈现出一种不确诊的模糊性,“药”则经常处于缺席状态,而与此相对的却是病人明确而具体的“死亡”。这种情节结构的处理,是暗含着鲁迅对我们前面谈到的他自己的“疗救文学观”的一个质疑:他越来越发现,自己不仅不能承担“治疗者”的角色,连充当“诊断者”也是勉为其难。正如论者所说,“鲁迅的深刻之处与独到之处在于,他自始至终对文学的‘治疗效果’有着近乎绝望的怀疑,以及与此相关的,对文学家所承担的‘思想-文化’医疗工作者的角色有着深刻的怀疑”。但我想补充的是,鲁迅在怀疑的同时,又在坚守着文学疗救:他后期的杂文更是变成“匕首与投枪”,决定对“社会之疾”放弃“药物”,改做“手术”。
“‘病态’、‘病苦’、‘疗救’等等,都成了一种隐喻,它不仅显示了在鲁迅的视阈里,医学与文学的相通,更暗示着医学本身的社会学、政治学的意义”图为鲁迅短篇小说作品《药》中的版画插图。
3顽疾、濒死
激发文学创造和生命的想象
疾病让鲁迅直面死亡的同时,还反而唤起了他的民间记忆与童年记忆,并激发了他的文学想象力与创造力。这样的“死亡体验”、“民间记忆”与“文学创作”的相互融合,是实在令人惊诧不已的
鲁迅逝世以后,他的主治医生须藤五百三写过一篇《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详尽地讲述鲁迅的病。据说鲁迅“自七八岁起即患龋齿,一直到二十四五岁,都在担心脱牙和临时应急”。因为牙齿不好,鲁迅肠胃的活动力也被削减,后还出现便秘、结核等病症。鲁迅的最后病情报告“追加疾病名称:胃扩张、肠弛缓、肺结核、右胸湿性肋膜炎、支气管性喘息、心脏性喘息及气胸”。
我们要讨论的是,鲁迅这样的衰弱多病的体质,对他的精神气质有什么影响?他的可以说是在疾病的煎熬与死亡阴影笼罩下的写作,是否也给他的创作带来某种特质?
我们在《鲁迅日记》里得知,在年9月1日至年1月,鲁迅肺病复发(年因兄弟失和也发过一次)长达4月余;年鲁迅最后病倒时写信给母亲,就提到年、年这两次病,以为病根就是当年种下的。一位“在上海唯一的欧洲肺病专家”称鲁迅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说如果是欧洲人,早就死掉了。这也说明,鲁迅的几次重病,都是直接面对死神的。而有意思的是,正是在~年与~年间,鲁迅的创作出现了两个高峰:鲁迅的《野草》、《朝花夕拾》、《彷徨》(部分),以及《故事新编》(部分)、《夜记》(未编成集)都分别写于这两个时期。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两个生命的特殊时期,鲁迅写出了《无常》()和《女吊》()这样的描写家乡传说、戏曲里民间鬼的散文,并且都堪称鲁迅散文中的极品。这就是说,疾病让鲁迅直面死亡的同时,还反而唤起了他的民间记忆与童年记忆,并焕发了他的文学想象力与创造力。这样的“死亡体验”、“民间记忆”与“文学创作”的相互融合,是实在令人惊诧不已的。
这里我们就不能不说到鲁迅对死亡的态度。鲁迅曾说,他是死亡的“随便党”。但他也和普通人一样,想过“死后怎么样”的事情。早在年他就写过一篇《死后》,说人不仅没有“任意生存的权利”,也没有“任意死掉的权利”。而当真正要面临死亡时,他又在想什么呢?年10月17日午后,鲁迅逝世前最后一次出门。他来到日本朋友鹿地亘的家里,送去了《女吊》这篇文章,并且和他们夫妇俩大谈日本和中国的鬼。在此之前,他还写过一篇短文,讨论“死后的身体”如何“处置”的问题。他表示:“假设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吃”。“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而“赖皮狗,只会乱钻、乱叫”。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神往的境界:鲁迅死后,他的生命化作了民间的鬼神,化作了“在天空”飞翔的鹰隼,在“岩角,大漠,丛莽里”行走的狮虎……这就意味着,鲁迅愿意用浪漫主义的幻想让自己超越医学意义上的疾病与死亡,永存于文学的梦里。
4医学、文学
都要使人“健康、快乐、有意义的活着”
今天中国的医学问题、文学问题、社会问题,也集中体现在“诚”与“爱”的缺失。大家议论得最多的所谓“医患关系”问题,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医生与病人之间失去了基本的诚信与爱。而我更要强调的是,医院,其所显示的却是整个社会的病症,而不能单单归责于医生、医院和病人
“医学”与“文学”看似不相干,却在鲁迅身上得到了共生。而其实,这两者本身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同通之处。
首先,医学和文学都面临同一对象:人。这看起来是一个常识,但却很容易被忽略:文学家往往热衷于直接表达思想、讲故事,而忽略了写人;医生们却常常只见病,不见人。
其二,医学与文学的对象,都是个体的生命。文学最应该 同时在我看来,医学与文学,都是“生命之学”。但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却常常陷入片面,除上面所说的忽视生命的个体性之外,我们还往往忽略了生命的整体性。这大概是受西方科学主义的影响,分工过细,眼睛里只有具体器官的病变,而不能从人的整体生命,各器官之间的关系中去把握病情。
其三,医学与文学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要使人“健康的,快乐的,有意义的活着”,这也应该是我们中国改革的目标,教育、文学、医学的共同目标,更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目标。这一点,很多医生大概更有体会:人们都是因为不健康、医院来的。我们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就是通过治病,使这些人成为“健康的,快乐的,有意义的活着”的人,这就是医生工作的意义所在。而在这里,不仅要使病人走出生命的病态,医生自己也要“健康的,快乐的,有意义的活着”。在我看来,当下中国医学、医院出了许多问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医生自身的身心健康出了问题,活得很累,并且看不到从事医务工作的意义。医生天天面对的是人的病态,这就需要文学、艺术的补充。文学、艺术虽然也会涉及人性的病态,像鲁迅这样主张文学疗救作用的作家的作品更是如此。但即使这样,鲁迅作品里的黑暗仍充溢着光明,是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力量的。文学与艺术的魅力在于永远能够引人走向真、善、美的境界。我由此而理解了,为什么许多杰出的医生,都有阅读文学作品、欣赏音乐、美术的业余爱好,这不仅是为了陶冶性情,舒缓职业的疲累感,更是为了坚守对人性的真、善、美的信念与追求。这也提出了医学管理学上的一个问题:如何营造一个更为“健康”的,医院环境和氛围。
此外,我们在前面介绍了鲁迅是以“诚与爱”之心,去从事文学、看待医学的。这应该是医学与文学更为内在的一致和最基本的伦理底线,也是医生和文学家的基本素养与品格。而今天中国的医学问题、文学问题、社会问题,也集中体现在“诚”与“爱”的缺失。大家议论得最多的所谓“医患关系”问题,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医生与病人之间失去了基本的诚信与爱。而我更要强调的是,医院,其所显示的却是整个社会的病症,而不能单单归责于医生、医院和病人。
上面说到,鲁迅“弃医从文”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他的文学气质不适合学医,也就是说,医学与文学是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心理特点和情感方式的。但即便如此,医学的科学思维与文学思维也有相通的地方。鲁迅在选择从文以后,特地写了一篇《科学史教篇》,强调科学也要有“美上之感情”,“明敏之思想”,更提出“科学发见(现),常受超科学之力”,是离不开“圣觉”(灵感)与“神思”(想象)的。他认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人性之光”,因此特别要警惕“惟知识之崇”,那是会使“人生必归于枯寂”的。我由此想到,许多有经验的老医生,常做出许多普通医生想不到的正确诊断,其中就有建立在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基础上的直觉与灵感。而医学想象力,更是贯穿在疾病诊断过程中的。追溯病因、作出诊断,都需要建立在深厚的学养与经验基础上进行假设、想象。在我看来,医学的魅力,就在于医生每天都在破解各式各样的“哥德巴赫猜想”,医生的快乐也就建筑在这样的创造性的劳动中,这一点是与科学家、文学家、教师的创造性事业相通的。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详尽地讨论了“疾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的关系。其实,疾病的隐喻意义是远超出了文学的。前面提及的“东亚病夫”就是对我们整个民族危机的一个隐喻。当年毛泽东就把对“病”的隐喻运用到党的整风运动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上,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今天的政治、社会生活里,也随处可见这样的医学隐喻。在这样的语言现象的背后,隐含的是医学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的联系,而且这样的联系,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密切,医院的问题常常成为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医患关系问题成为全社会 更重要的是,随着我们对现代人认识的深化,发现人生理与心理的疾病是很难决然分开的。因此,对疾病的治疗,也必须是综合性的。从更长远的发展看,虽然专业的分工还将存在,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综合发展已经成为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正面临一个全面变革的前夕:不仅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而深刻的变革,更是包括医学、文学在内的理、工、文科,以及文科内部的文、史、哲各科的发展及相互关系的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对此,我们准备好了吗?
这也引出我们最后要讨论的一个关系医学学科发展的问题:该如何为医学的学科性质定位。长期以来,我们都习惯于将医学视为自然学科。但现在,医学内在的人文因素逐渐显露,在医学生理学、病理学、临床医学等传统学科之外,又出现了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医学哲学等新概念或新学科。在我看来,医学的人文性,是由其对象是“人”这一基本的特质决定的。因此,我斗胆提出,我们是否也可以把“医学”定位为“人学”,一种具有自己特点的“人学”。这样,既可以揭示医学与其他以人为对象的学科,例如文学、哲学、伦理学、法学等等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可以更深入地揭示医学区别于文学、哲学等的独特的“人学”内涵。在现实的医学实践里,则能够引导所有的医务工作者把 以上为《健康报》原创作品,如若转载须获得本报授权。
北京白癜风断根治疗的医院郑州白癜风医院